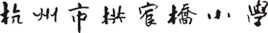二
统治者为了把这类城镇变成由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政治中心,又在这些城镇中,设置不同级别的官暑,驻扎重兵,兴修学宫,把封建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因素强行加于,使之完全纳入了封建王权控制下的城镇体制的轨道。
临清,在“前明嘉、隆时,庙堂之上响意此都”设有“文武重臣,分巡弹压。”明弘治前,临清县制,属东昌府。弘治二年,由县升为州制,领馆陶、邱县二县。清初临清因明制,乾隆四十一年,临清更升为直隶州,并领武城,夏津、邱县三县。故自明弘治以来,临城就是州级官暑所在地。据史籍记载,自明至清,在临清就设有州暑,州同暑,州判暑,巡检暑,协镇暑、都司暑、兵备道暑、临清卫暑、都察院行台、布政司、按察司、山东卫河提举司、工部都水分司监修漕艎暑,山东督运把总暑等不下二十多种封建官署。此外,早在明永乐初,于临清就设置了工部营缮分司。宣德初,封建政府于大运河一线设钞关十一处,临清即为其一。由此又在临清设置了户部榷税分司暑。嘉庆五年,又增设闸务等封建掠夺机构。以上各种封建官署机构,历代虽稍有裁革,但大部分被清代所承袭下来。
为了“防微杜渐”,封建政府始终没有忘记“兵戎实为先务”的原则。清乾隆十四年。临清知州王俊对此深有感触地说:临清为“扼要之地,故前代多宿重兵于此。今犹置副将一员镇守,当四海入安之时,武备亦未可尽驰舆”。因此,自明清以来,临清就是一个“戎卫之兵,方屯此间”的地方。据《临清县志》载:“明代设总兵官驻临之,兵于时最多,临清顺治元年仍明制,设临清镇领左右二营,另设旗鼓中军守备。四年,添设中、前二营,并左、右为四,共兵四千名”。后经裁革,乾隆二十七年,“本营所辖余马兵一百四十八,步兵五百六十二名,……嘉庆二十三年,……额存马步兵五百三十余名,……以外尚有马快民壮等数十人,可缉捕盗贼之责,共资防御。”这些兵力除镇守临清外。还分防临清周围六个地区,以达到封建国家机器直接镇压的目的。
在封建政治、军事强化的同时,封建的宗教伦理意识形态也随之渗透到临清的政治生活之中。与临清筑城的同时,作为封建宗教文化的主要代表—孔庙,即在修建之中了。对此,明人张元祯在《儒学新修记》中把封建官府兴建孔庙,提倡儒学的目的做了露骨的表白:“天子命吏司一方,风教必潜有以寓鼓舞之机,庶少足以诩文明之化,政有似缓而急,似清而重,兹庙学突然。”有清一代,历朝封建官僚都把修葺孔庙儒学当做“有司之要务”,使临清的孔庙儒学形成“阕里而外,清源规模最”的局面。至此,临清已成为在运河北部地区“具有牧学校,有师而兵行之备”的封建政治、军事、文化的统治中心点了。
济宁在运河南部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自有明一代济宁就是府州级治所所在。清因明制,济宁州隶属 州府,领嘉祥、钜野、郓城三县。乾隆四十一年,济宁升为直隶州。领嘉祥、鱼台、金乡三县。济宁除了有与临清相同的州治官署等封建官僚机构外 ,在明清两代因济宁有“唯都水监之所驻节,故公署特多于他郡”。此外,明清两代为了治理运河,在济宁还设有负责整个运河事务的总督河道部院。并设有配合管理运河、督促漕运的管河兵备道军事机构。因此,济城的封建军事色彩更显浓厚。明万历三十七年,曾任济宁管河兵备道的王国祯称:“国家定鼎燕京,仰籍东南,岁漕四百万石以给京师。惟是漕渠一脉为之咽喉。漕渠通塞,国计盈缩以之,漕故重。且此地水陆要冲,四方商旅杂处,货财萃聚,畔孽萌生,易为饷道梗。永乐初,会通河始开,曾命大司马统兵十万镇守济宁矣。”清初,“河帅(即兵备道一引者)所统虽以防河为专责,而镇守亦赖之以为重。”为了进一步加强济宁城的镇守,清政府又“特设城守一营。”为了统一调配,清统治者在“防河与防城无非捍卫斯民也,岂得歧而二之哉”的理由下,由管河兵备道所统的“河标三营,”加之“城守一营,”四营兵力皆统于河帅摩下。从顺治至康熙年间,四营总兵力始终保持在四千名左右。后经康熙后期裁拔抽调,雍正,乾隆直到道光年间,四营总兵力仍拥有一千五百名左右。在驻有国家正规军的同时,济宁的封建官府还积极筹建地方武装团练组织——“又勇。”济宁的地主武装团练的历史可追溯到明天启年间。据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记载:“州境向有团练,记载犹存,军兴以来,师其遗制,扩而充之,与大兵互为犄角,以助声援。”明天启年间的徐鸿儒农民军攻打济宁的失败,及崇祯甲申李自成义军的将领郭升占据济宁的失败后的被残杀,都是封建官府军队与当地地主武装团练共同镇压的结果。清道光年间,济宁世族,团练头目孙毓桂在《义勇记略》、《团练记》中称:“济宁义勇之设与练勇相辅而行,法至善也。义勇局共二十处,… …按户抽丁数以万计。演枪炮,习技艺,数月之后分期输赴教场,合阵操练。其枪炮联络,技艺娴熟。… … 每遇大会合阅,旌旗飞扬,矛戟森列,虽绿营行阵不是过也。义勇如此可谓绝无仅有者矣。……总之,练勇为义勇纲领,义勇为练勇犄角,二者相权,”“济州团练遂为山左之冠。”
在封建政治,军事势力强化的同时,济宁的儒学之风为盛行。正如清康熙年间的总河靳辅所云:“济宁,故任国也,其距阙里也仅二舍余,… …圣贤教泽渐被而涵濡之也。… …则察厉学校若是其重以 也。”在“无礼义则上下乱,岂不关乎人事焉”的封建伦理道德指导下,自明以来,济宁州各地“无不庙祀孔子,无不立学。”济宁的孔庙学宫大都兴建于金元明三代。金元明时,孔庙学宫的规模“纵关关广仅若钱丈。”清继明后,历代对孔庙雪宫屡有兴修,特以康、乾年间为最盛。历代知州上任后,都把修葺孔庙学宫作为首要任务。乾隆四十二年,知州兰应桂大修孔庙学宫,“耗费白金九千连两。”其规模遂之扩展到“周垣—百六十余丈。”道光二十一年知州徐宗千“于捐修城工案内拨款修理,”使孔庙学宫内的“塑像及礼乐器皆新之。”这样,济宁经历封建统治者的精心营治,终于成为一座“文武冠盖”可“与首郡匹”的重镇了。
张秋镇在明代属于兖州府东平州,由寿张、东阿、阳谷三县管辖。清初,张求镇所属府州县因明制。因张秋镇地处三县鼎峙,横跨运河,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向有“南北转运锁钥”之称,自明以来就为封建政府所重视。
明景泰年间,寿、东、阳三县王薄分暑张秋,张秋始立三县管河主薄厅。成化年间,“开会通河,特遣都水大夫一人驻节其地,以总漕渠之政,”张秋又设有都木分司暑。自明弘治四年后,“张秋河厅始有专设,注以通判任。”至嘉靖四十三年,又“添设捕盗通判,”用以“弹压一方,”这样张秋又设有捕务管河厅暑。此外,自明代在张秋的封建官僚机构还有都察院、布政司、巡检司、税课局等。这些封建官府机构虽有废弃,但象捕务管河厅 暑,工部分司等重要统治机构仍被保留下来,并成为在张秋的常设机构。明清两代,张秋镇除设有种种封建官暑外,封建官 府在张秋还建有 藏大批漕粮的水次色。这些漕粮大都是从运河一线各县搜刮来的田赋,先集中张秋,然后转运京师。
封建政治统治与军事控制往往交织在一起。封建官府以“本镇为漕贡咽喉,南北枢地。有城池而无守御与无城同,有士伍而无训练与无士同”为借口,在张秋“民兵本镇旧无” 的情况下,为了防御“流寇犯境”与“以杜奸伪,”兵自正德间… …始议设守御,先是操兵籍、市中、丁力谓之市民,已乃革去。第以十家为牌,每牌除占役外,随多寡编其队伍,春秋赴教场操演,府捕所主之。”这样,张秋实际上就成为一座平时“即隐然虎豹在山之势,”遇有“奸侠”“匪情”便“能驱市人而战”的大兵营了。
在文化思想方面,张秋镇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康熙二十八年,张秋通判史在雍的一段表白可谓把兴建庙学的原因与作用做了绝好地说明:“官民者必本于教化,而教化莫先于崇圣。使不建文庙以奉先师之祀,则官吏之瞻拜无由,… …有文庙则可以敬宣上谕,可以讲读律令,… …而后可以无旷厥官矣。”因此,在“有城池则必有学校”的原则下,自明嘉靖年间,张秋就有文庙、书院。清代历任通判并屡有修葺,经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的营治,张秋镇遂成为“雄城雉起,万瓦驿集,至公廨津梁、神祠、梵宇、逵术、井板经制大备,若盖齐鲁间一都会”矣。
正因为临清、济宁、张秋是各级封建政权治所在,同时驻有大量军队,因而在这些城镇中也往往寄寓着大量的达官贵人,地主缙绅与奸商大贾。据史料记载;临清在明代复加疏凿运河后,“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开府分曹,达官要人之所递临。”济宁地处“南北着交,而物产人物之盛甲于齐鲁,于是名士巨卿,文人墨客往往安其风土而寄迹焉。”因各地“缙绅冠盖往往侨 ”济宁,故史籍有济宁“侨寓特多”的记载。据《寿张县志》载,寿张县的“士宧之族为盛,亦多在张秋。”大量地封建贵人集中在临、济、张这就更增添了这类城镇的封建色彩。
由于临、济、张都为封建基层政权的所在地,因而也就成为封建王权在地方统治的象征,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为历次农民所攻略的目标。据史籍记载:从明末到清中期,临清就被李自成(明崇祯甲申年),寿张王伦(清乾隆三十九年),太平天国(清咸丰初)等农民义军攻占过。济宁也曾被徐鸿儒(明天启二年),李自成(明崇祯甲申年),捻军(清咸丰初)等农民义军攻打与占过。张秋也不例外,明末崇祯十四年,梁山李青山农民义军,“列其众,分攻寿郓等处,原寿张县步弓手维岳(号曰丁明吾)会集周魁轩农民义军“万余”,破寿张后,遂攻打张秋,给封建统治以重创。
总之,通过对临清、济宁、张秋三城镇的考察,使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镇都是封建政府根据其统治制度的编制,特别是根据其防务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兴建。使之成为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明到有一代,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与封建国家机器的不断强化,作为封建王权在地方的统治中心也相应不断加强与强化。尤像临清、济宁、张秋 ,地处维系封建国家经济命脉的漕河之上,这就加重了它们的政治军事地位,其封建色彩也更显浓厚。